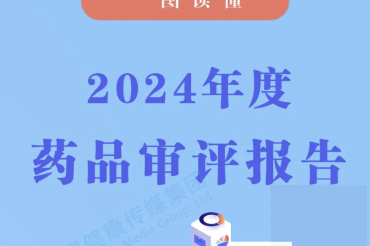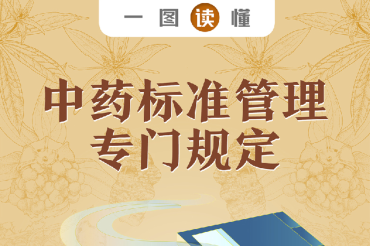略論《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免責條款之修改
- 2021-11-02 11:10
- 作者:鐘震球
- 來源:中國食品藥品網
新修訂《行政處罰法》已于7月15日起施行。新法確立的“過錯推定”歸責原則,將對行政處罰的實施產生深遠影響,也為《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的修訂帶來了契機。筆者擬對《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2016年修正)第75條(以下簡稱藥品免責條款)的修改提出淺見,旨在拋磚引玉,為條例的修訂集思廣益。
藥品免責條款為行政立法之創舉
現行《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75條規定:藥品經營企業、醫療機構未違反《藥品管理法》和本條例的有關規定,并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銷售或者使用的藥品是假藥、劣藥的,應當沒收其銷售或者使用的假藥、劣藥和違法所得;但是,可以免除其他行政處罰。
藥品免責條款在理論和實踐上具有開創性意義,在行政處罰中率先引入“過錯推定”的歸責原理,客觀反映了藥品經營使用環節某些違法行為的特殊性,彰顯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取向。通過近二十年的實踐,其理論的正確和實踐的可行得到充分驗證。新修訂《行政處罰法》確立了“過錯推定”歸責原則,將深刻影響藥品監管部門行政處罰的實施,亦涉及相關法律法規的修改和完善。
過錯推定歸責原則的性質和特點
行政違法責任的歸責原則是指確定行為人承擔行政違法責任的一般準則,通常包括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等。在此次《行政處罰法》修訂之前,我國行政處罰主要實行無過錯責任原則。依據該原則,在行政違法責任的構成上,不將主觀過錯(故意或者過失)作為違法行政責任的構成要件,無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只要實施了違法行為,都應受行政處罰,且違法行為的舉證責任全部由行政機關承擔。過錯責任原則則將主觀過錯作為違法責任的構成要件,認為行為人必須存在主觀過錯,才能承擔相應的行政違法責任,并應由行政機關舉證證明。
《行政處罰法》第33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上述即過錯責任原則之特殊表現形式——過錯推定原則,其要旨是行為人一旦實施了違反行政法律的行為,除非其能夠證明自己主觀上不存在故意或者過失,否則法律上就推定行為人具有主觀過錯,應當承擔相應的行政違法責任。實行過錯推定原則,兼顧公平正義和行政效率,平衡公眾利益與行政相對人利益,符合法理,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要求的正確選擇。
過錯責任與過錯責任推定的區別在于舉證責任分配的不同。實行過錯責任,證明行為人存在違法行為及主觀過錯的責任由行政機關負責;而過錯責任推定則不同,行政機關發現行為人有違法行為的,一般先推定行為人有主觀上的過錯,而無須主動查證當事人的主觀狀態。如果行為人認為無辜不應受罰,進而提出證據證明不存在主觀過錯,則行政機關不予處罰。
藥品免責條款中亦隱含“過錯推定”的原理,“藥品經營企業、醫療機構未違反《藥品管理法》和本條例的規定,并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銷售或者使用的藥品是假藥、劣藥的”,其中行為人與行政機關共同承擔“未違反法律有關規定”的證明責任,行為人獨自承擔“不知道所銷售或者使用的藥品是假藥、劣藥的”即沒有主觀故意或者過失的證明責任。
不予處罰與免除處罰的法理分析
《行政處罰法》自始至今未設立免除行政處罰制度,僅規定了不予行政處罰的情形,如第30條(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有違法行為的)、第31條(精神病人、智力殘疾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時有違法行為的);第33條第一款: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第二款:當事人有證據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等。“免除處罰”主要見于行政法規及規章中。
不予處罰與免除處罰,結果看似相同,最終行為人都無需受罰,實有本質區別。《行政處罰法》第四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并由行政機關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實施。
行為人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為并非必然受罰,其行為須達到“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條件,也即符合行政違法責任的構成才受罰。依據法理,行政違法責任的構成應當符合四個要件:(1)主體要件:具有責任能力的組織或者個人;(2)主觀要件:行為人主觀存在故意或者過失;(3)客觀要件:違法行為及其后果;(4)客體要件:由法律所保護并為違法行為所侵害的行政管理秩序。一個行政違法行為只有同時具備四個要件才能給予行政處罰。
“不予處罰”的實質是主觀要件的欠缺,即行為人主觀上不存在故意或者過失,從而不應受罰。免予處罰之本意是當罰而免,即一個行政違法行為,已經具備了違法責任的四個構成,本應承受行政處罰的制裁。但是基于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限制及某些行業的特殊性,在一個時期內難于克服的某些違法行為,其社會危害性及后果輕微的,立法規定可以免除行政處罰,以實現“處罰與教育相結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自覺守法”之立法宗旨。在一定意義上說,“不予處罰”與“免予處罰”的區別可若宣告無罪與免予刑事處罰。
立法者在制定藥品免責條款時,雖然表述為“免除其他行政處罰”,其實質依然是“不予行政處罰”。在執法實踐中,免責條款涉及的假劣藥品絕大多數都是常規檢查驗收無法發現,最終經法定機構檢驗,結果為不符合國家藥品標準規定的藥品。在藥品經營使用環節客觀存在著行為人守法盡職、循規蹈矩,盡到行業公認標準的注意義務,也難于通過常規檢查發現產品的外表及標簽標識瑕疵之外且大多為出廠時已經存在的內在質量問題。此類非法產品仍然可能購進并銷售、使用。此種情形下的行為人守法盡責,在主觀上不存在故意或者過失,不符合行政違法責任的構成,因而不應該受罰。
藥品免責條款的修改思路
《行政處罰法》第3條規定:行政處罰的設定和實施,適用本法。遵循《行政處罰法》的立法思想和基本原則,依據“過錯推定”的歸責原理,總結和吸收近年來立法機關在健康產品監管立法上的探索與創新,修改藥品免責條款可謂水到渠成。
立法機關對《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的修改歷程可資借鑒。該條例于2000年4月1日期施行,期間于2014年2月曾修訂。在2017年修改之前,對于經營、使用不符合法定標準的醫療器械行為,不論行為人是否存在主觀過錯,均給予沒收、罰款等處罰(《醫療器械監督管理條例》2014年版第66條)。在2017年修改時增加了第66條第二款:“醫療器械經營企業、使用單位履行了本條例規定的進貨查驗等義務,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經營、使用的醫療器械為前款第一項、第三項規定情形的醫療器械,并能如實說明其進貨來源的,可以免予處罰,但應當依法沒收其經營、使用的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醫療器械。”上述修改初步奠定了行為人沒有主觀過錯時經營、使用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醫療器械可以部分免責的制度。2020年12月再次修訂,該條例第87條規定:醫療器械經營企業、使用單位履行了本條例規定的進貨查驗等義務,有充分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所經營、使用的醫療器械為本條例第八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第八十四條第一項、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和第三項規定情形的醫療器械,并能如實說明其進貨來源的,收繳其經營、使用的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醫療器械,可以免除行政處罰。此次修訂將可以免除行政處罰的“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醫療器械”進一步明確,且范圍有所擴大;將沒收“其經營、使用的不符合法定要求的醫療器械”改為“收繳”。在此之前,2020年6月國務院頒布的《化妝品監督管理條例》更是率先確立了對“不符合法定要求的化妝品”實行“收繳”的處置制度(第六十八條)。然而對于銷售或者使用“非法產品”之所得,醫療器械和化妝品免責條款未曾涉及。銷售或者使用“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產品”取得收益客觀存在,不應回避或遺漏。
上述行政法規引入“收繳”制度處置“免除處罰”案件涉及的“非法產品”是一項意義重大而深遠的創舉。“收繳”是一種行政處置措施而非行政處罰,其程序較為簡便,可以大大減少行政機關的工作量,且因為不屬行政處罰不涉及在政府誠信體系公開相關的信息,對企業的信譽影響微末,是一項利國利民的法律制度創新。對于不予處罰案件涉及的“非法產品”及“所得”,在法理和邏輯上已經不能再以行政處罰種類之一的“沒收”處置。從維護法治尊嚴和公平正義考量,對于不予處罰案件涉及的“非法產品”和“所得”,以“收繳”處置,符合法理,切實可行。
小結
綜上所述,筆者的修改建議如下:一是確立“不予行政處罰”制度,以“不予行政處罰”替代“可以免處其他行政處罰”,以羈束性取代自由裁量;二是確立“收繳”制度,對于涉案藥品和所得,取消行政處罰之“沒收”,以行政處置措施“收繳”替代;三是規范文字表述,將“有充分證據證明”修改為“有證據足以證明”。修改后的法條表述為:藥品經營企業、醫療機構未違反《藥品管理法》和本條例的有關規定,并有證據足以證明其不知道所銷售或者使用的藥品是假藥、劣藥的,應當收繳其銷售或者使用的假藥、劣藥和違法所得,不予行政處罰。(原廣東省韶關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鐘震球)
《中國醫藥報》社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使用。
(責任編輯:陸悅)
右鍵點擊另存二維碼!
-
為你推薦
-

執法實務|建立稽查執法五維坐標系,提升執法精準度
?藥品稽查辦案專業性強、程序復雜,如何從紛繁復雜的法律和事實中抓住核心、理清脈絡?筆者認為,關鍵在于堅持系統思維,構建涵蓋程序、文書、評查、法律、裁量五個維度的稽查執法坐標體系。 2025-09-26 10:49 -

執法實務|厘清證明責任?推進依法行政 ——淺談藥品行政處罰中的證明責任
在藥品行政處罰過程中,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以行政訴訟中的證明責任分配為主要指引,厘清其在處罰程序、處罰職權、處罰裁量等方面應承擔的證明責任,充分收集證據,并合理應用證據,保證行政處... 2025-09-24 08:49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10120170033
網絡出版服務許可證(京)字082號
?京公網安備 11010802023089號 京ICP備17013160號-1
《中國醫藥報》社有限公司 中國食品藥品網版權所有